西安彩钢房 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中心:文学散文中的冰冷躯体与生命之痛
- 手机:
- 微信:
- QQ:
- 发布人:佚名
- 所属城市:重庆
信息描述
西南学院创意写作中心
文
学
散文
创意|艺术|生活|想像
冰凉的躯体
吴子恒

父亲一开始说他只是头痛,我也是如此认为的。这天吃下午饭的时侯,他让父亲倒了一小杯红酒,刚喝下半口面目就显得惨白上去,之后一边的脸上抽动着,不停地用手搓揉着右半边头皮。那天往前再过半个月,父亲连扫路的活都干不了了,妈妈接替了他的工作。又是一个月,当接我出校车的人弄成我母亲而非是父亲或母亲的时侯,我能够察觉到淡淡弥飘动来的严肃之感了。
“你哥哥入院了。”妈妈面无表情地跟我讲。
“啥病?”我在电动车后排上小声问。
“不清楚!”我妈说,“脑子长瘤了。”
我想上去二姨母亲家的那种父亲,他似乎也是由于头痛死的。他死的时侯我没有去,丧礼我也没有出席西安彩钢房,其实由于我的大不敬,那种父亲在死后没几天就入了我的梦,亲切地管我叫“大儿子”。
脑中瞬间就浮现出了两位姐姐的脸孔,我想起父亲往日在家里责备我的脸孔,告诉我要好好读书的教诲,我想上去他那笨拙的自言自语的模样,想上去他说我装成小大夫,给他吃药却把他手打断的那件事——爷爷之后再不能啰嗦我了。我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接过锁匙,父亲停水火车的当儿,我打开家里红色的小门,潮湿的秋之气冲了我一脸,家里死气沉沉的,一个人都没有。爸爸说你们都去诊所了,今天她也会去,之后是妹妹接我,给我煮饭吃。我又想上去这位逝去之人的脸孔,不由自主地就将“死”这个字和父亲联系了上去,我吓了一跳,憭栗地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几天前,父亲还带着那副不怒而威的硬邦邦的脸孔,老成地训诫我要认真写字,不许潦草。
约莫两周后,进了十二月份,我快要放暑假的时侯,父亲和母亲她们回去了。但姐姐只在家里住了三天,就搬进了村庄田地的最东边的彩钢板房里。父亲之前告诉过我,二姨父亲的那种父亲,死之前就在那里渡过了最后的时日,父亲说涛叔跪在地上哭得缓不过气来……面前的父亲发愣地坐在简陋的椅子上,没有毛发,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疼痛,走路像失修的机器人一样。他的嘴巴蹦下来发颤巍峨的三个字,就像在空气中微微颤动着的冰晶通常:
“——吃…饭……都。”
我们所有人才沉默地动起餐具,不晓得是谁打开了电视,还刚好到了广告的环节。我想用呵欠掩饰一下我将落的眼泪,却在不经意的抬头之间瞥到了红着眼睛的母亲,她的身后坐着妹妹,眼睛枯黄,像冬天,像被冻烂了的农地。
“恒恒,给你爸爸倒杯水吧。”许久不曾开口的妹妹忽然对我说。
我和爸爸一样发愣地点点头,拎起桌边的水壶,往玻璃瓶子里倒了半杯,递到父亲的手里。他的左眼冰凉而空洞,嘴角似乎还浮动着奇特的笑容,我把杯壁温热的瓶子递给他,父亲的手像风一样冷,似乎冷掉了一样。我忽然倍感莫名的焦虑。但那其实是我爸爸啊!我如是想道,回头看了看沉默的母亲,母亲摸了摸我的头。
父亲不再熊我了,他不再给我讲好多年前他一个人在西北独闯的故事西安彩钢房,我妈妈也不再从一旁附和或修正他的话。我趁势也没有写我的作业,上公厕的时侯,在我们家最中间联接炕屋和厨房的大卧室,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在煮饭壶旁,空旷地跟老师打着事假的电话。二年级的时侯,同伴姓徐的女孩儿也以前由于类似的事情一天没有上课,站在徐的空位儿前告诉我们这事儿的朋友还依稀带着艳羡的语调。接出来的一周,我都没有去中学。
往年走这条穿越田地,通往村外的大路,都是为了串家在另一村的同事二姨父亲家的门。此次却是为了看昨天晚上就迁往村边的爸爸。话照旧是由爷爷说给我听的,她之前丧失那种俏皮的,我很喜欢的小儿子的时侯,可没有如今这样坚强:
“恒恒,你父亲昨天就走了。你得记着他,昂?”
我默认地点点头。在确认是否要带我来这儿之前,我偷听着父亲她们在炕上那屋的谈话:
“小孩儿去看死人,不好!再说那地方也霉气,谁家人要死都往哪里送。”
“那哪里有这一说呢?我小时候,大家领我在西北,那谁家死了人还稀少呀?也没见有哪些事儿!”
“恒恒才多大,十岁的男孩儿,不用非得去唷。”
“——那必须得去看!再如何着,那是我爹,他爸爸!霉气不是那么个霉气法的!”这是一个空灵的喉咙,我不需思索都晓得是谁的声音……
小径的入口左首开始出现没人居住的毛坯水泥房,左侧是凹进去的一片洼地,上面尽是他人图便捷丢的垃圾。所幸现已入了冬,穿着鹅绒服或衣服的我们能免受恶臭的熏扰。透过离散的几棵柳树还能看到前面平旷的菜园,我想上去那三四年前的事情:爸爸和妈妈骑着两轮车,车斗里装着农药和我,我在树下自己玩,探求虽然被废弃的水井房,听着背后传来的若有若无的祖父亲的言谈。
——彩钢房到了。它隐藏于冬日的稀疏的树间,树干们争前恐后地伸向它的红色铁壁,像病危的枯黄右手。房内不仅一张木架子床和一个和桌子几乎一模一样的椅子外,哪些都没有。父亲的两个亲兄弟就站在床边,一言一语地烧尽着家中所剩无几的吵架。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消沉的脸,母亲这以后更是捡上去投掷许多年的毒瘾——爷爷说不出话来了,耳朵只是一眨一眨地保持着最后的模样。我跑过去跪在床边,却没想到双膝一沾到地面,我的耳朵就只能看到床架和简陋的毛毯,于是我就微微举起身子,嘴还不留神磕了一下。就着血的甜气味,我痛楚地流了泪,在父亲床边卑贱地宣泄上去……此前,我认为流泪很丑恶,我想上去爸爸,妈妈,母亲,母亲,她们此前都叫我不能流泪,但我偏偏非常爱哭,尤其是上幼儿园的时侯,哭得会比现今还要惨重十倍。抛去了面子,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了下去,她们都说我真就是父亲的女儿。我抹了抹泪,躺下挪到屋外看天又看地,砭人的风一吹,我就想上去方才我跪在那里的样子。我的父亲,他死了,他的手是那样冰冷,似乎现今的寒风一样凄厉。他右手上若树根的纹路,晦暗若黑夜的光泽,陷入的脸颊,这些尖刻的话语——一切都过去了。西边聚了一堆云彩,黑亮之中有两抹条纹,自哪里闪烁着雷电的光辉,阴沉的战鼓也急剧传来……
在我面前,在记忆中的自我看来,父亲身着西服,怕事,双手双脚直挺挺地立着,下摆的袖子同裤子一样,和我一直保持着一定冰凉的距离地去了。父亲的已逝是这么没有逻辑,似乎他前一日还很正常,第二天就因各类意外车祸而出人预料地离人而去了似的。父亲这个人原本就爱说一些没有人情味的离谱的话,比我母亲她们还要更进一步地鞭策我前进的脚步。
幼儿园的时侯——我对这一时期的记忆本就模糊——爷爷告诉我是我把他的手给打断的。当时我有几根从村医院用来的空针头,没有针筒,我抡起着针筒给家里的所有人验血,吃药,挂点滴。父亲在家的时间相对较长,我就总拿他当患者对待。记忆旋即就跳到了炕屋那里,父亲在炕两头的墙面上用电锤钻孔,用类似金属力臂的东西帮助父亲把身子撑上去——那时侯我才晓得是父亲的手断了。我惊愕地扔掉了所有的针头,内心泛起一缕缕羞愧。或许爷爷的手就是由于我才断的吧!但后来又是某三天,我发觉爸爸相安无事地从房门里走入来,炕屋那里的装置也拆了,爸爸的双手更是完善完好。我的罪责一瞬间消失了。
事假的一周之后,中学要组织期终考了。妈妈她们决定还是让我把最后的课上完,最重要的是把试考完。复学的第三天,天上飘着细微的雪花,而后就密密妈妈地下成了浓雾通常洋洋洒洒的大雨。原本的七天,我都没有玩雪的兴致。整座城市都覆盖着淡漠的雪衣,我所想到的却只是那恼人的湿滑桥面;念书路上父亲此前常带我去的那条河上冻了,我脑中也没有往日赛事在冰上滑沙子的记忆,而是见到肃杀冬景的悲凉。我们到了中学,一个接一个地下校巴,坐进寝室里机械地晨读。窗前小雨依然,寒风溜进课室,穿着鹅绒服也暖和不上去。我怀疑寝室里是不是只有我感觉冷,她们都还是同往日上课通常的认真。有人传闻,城里的雪越下越大,我们要提早休假了!我不以为然,直至考试前的最后三天,我们提早在下午就被通知下班了,我才发觉操场的雪早已足以没脚了。
这样的天气只能安静地等待父亲来接送了。老师下达了做作业的任务,自己转身就钻进了办公。有几个人忽然就结伴背书包冲出了寝室外边——仔细一看,原先操场那里早就积满了打水仗的人。我点燃了一点兴趣,嘟囔手里的笔,看着课室的人走了大半,也背起书包到了操场那里。我想起来家里人常告诉我这样疯玩的女儿都不会好,父亲也曾说过,学习滴人总比玩的人强……我的手此刻非常冷,冷到搓揉眼珠都不会认为有一丝剌激感——在这样的雨天,没哪些大不了的!我放下书包,见到了同班的朋友,我们相视一笑,“歘”地一下冲往前去,推搡在落雪之中。冰雪呼在身上反倒会倍感性感辣的,我被人按在雪里呼吸了一会儿,彻骨的雪气透过鼻子伸进我的身体——冷啊,比冬天还冷!我忽然就站躺下来,推开一旁的朋友,想着要狠狠地反击他。我冷静了一会,身子逐渐脱离了情绪的掌控,这反倒使我更加意识到周边的严寒。我看到虽然有如此多人,操场还四处是仍未被打扰的落雪堆,它们就这样无声地向我传达着阴冷的讯息。
我似乎意识到了哪些他人未曾发觉过的可怖事实一样,突然就不敢再玩下去了。我当心地背起书包走出了操场,把手藏进鹅绒服兜里,盼望她们能很快就显得暖上去。我总算在快要走出中学时错愕地望了望那一片片积雪,我不敢在像刚刚那样肆意地砸雪、扬雪。我担心,其实就在哪一处被积雪覆盖的地方,其实就在我忍不住俯身团雪球的时侯,里边的雪里就藏着同雪一样冰凉的父亲的右手……也许,父亲那副冰凉的躯体,如今就安静地躺在地上,埋在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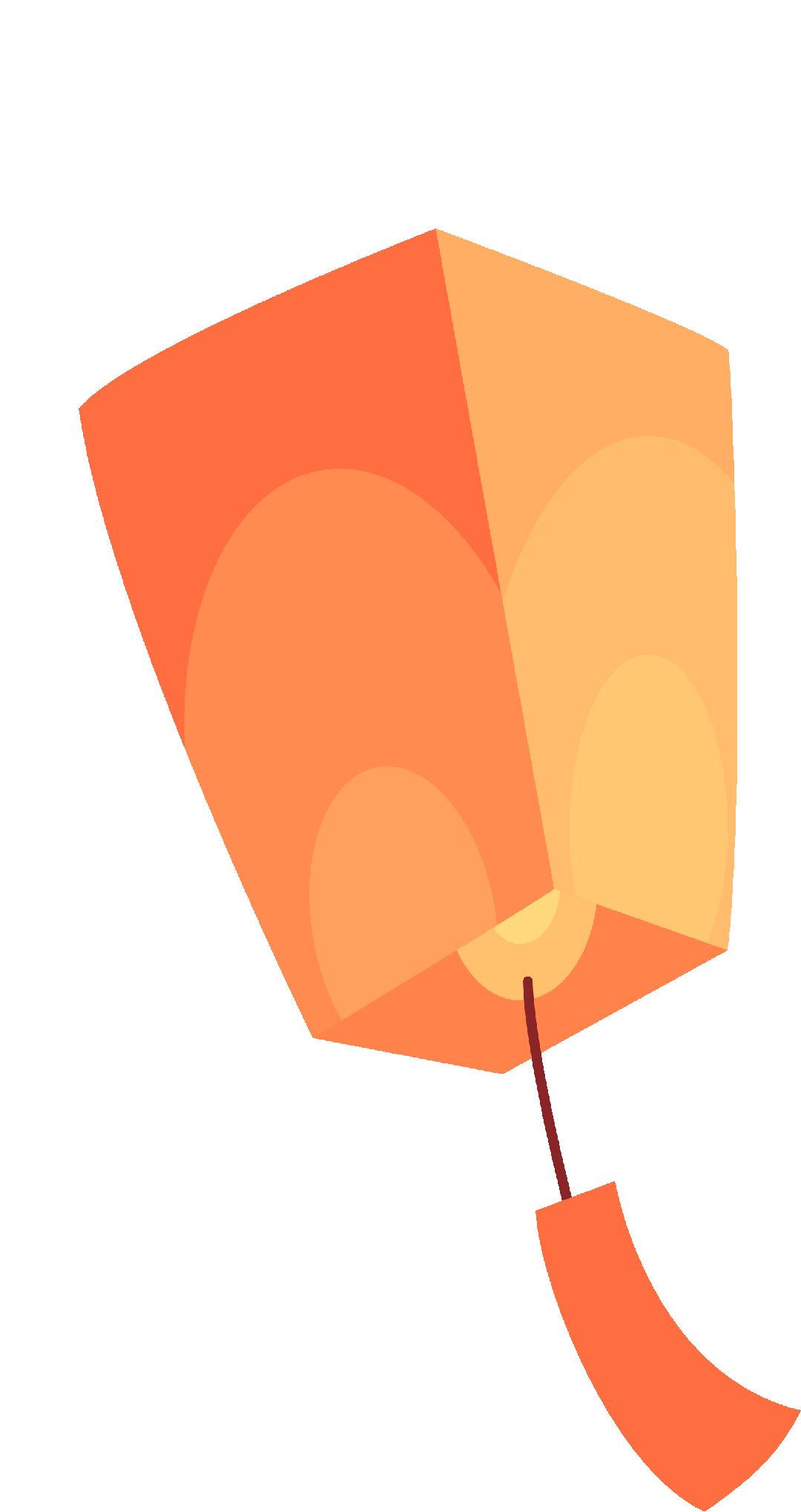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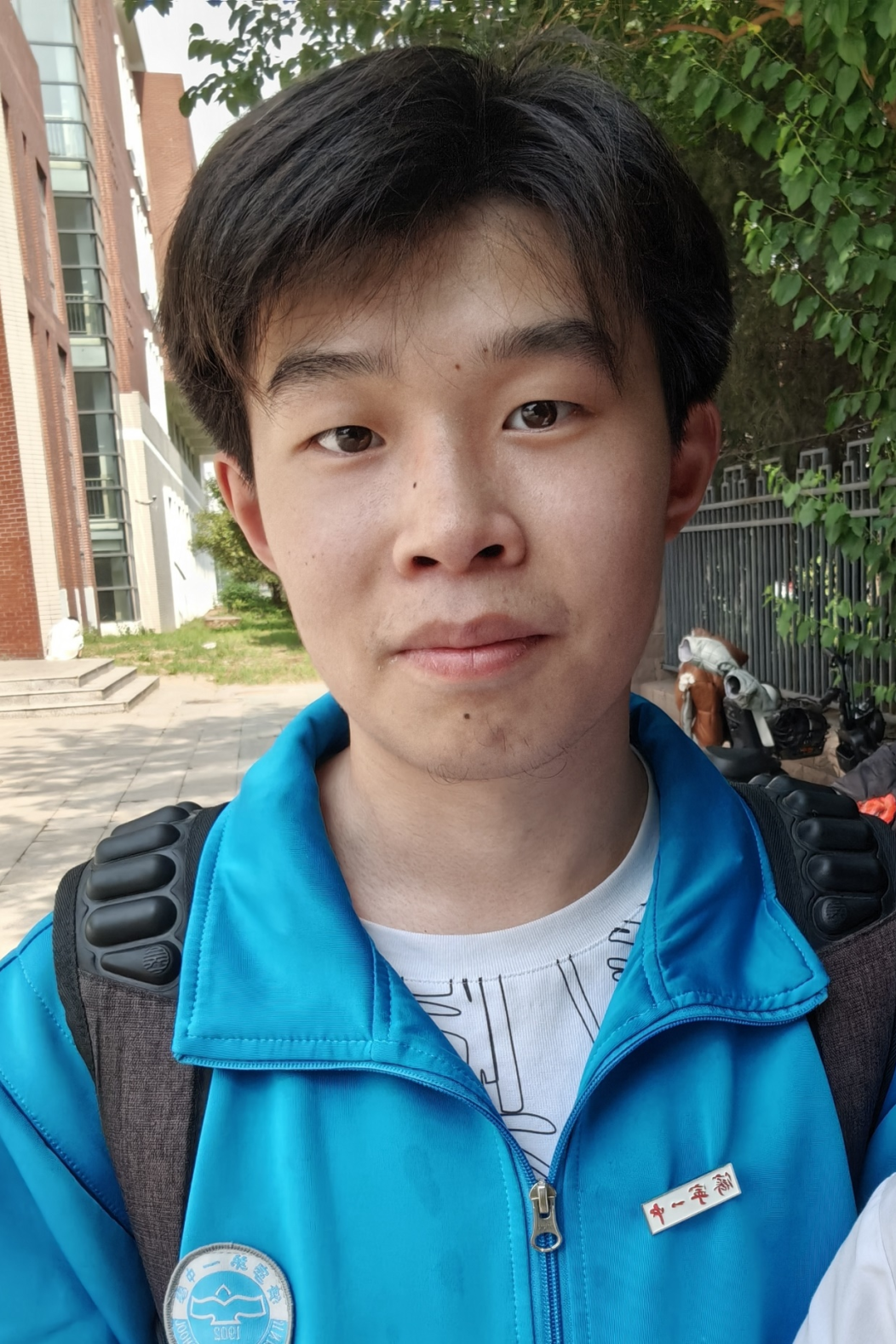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bouttheauthor
吴子恒,杭州外粤语学院翻译专业大二在读,喜欢阅读。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二手彩钢网看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