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彩钢房多少钱一平方 百年梦 泉乡魂:林甸记忆征文活动,邀您共述乡愁与难忘岁月
- 手机:
- 微信:
- QQ:
- 发布人:佚名
- 所属城市:重庆
信息描述
编者话:、“林甸旧事”微信公众平台与林甸温泉湿地文化沙龙联合举行,即日起,我们将相继择优刊载收到稿件,希望更多乡友、省内外各界同学参与征文,提高百年林甸著名度。征文投稿电子信箱:zlxaaa@163.com
“百年梦泉乡魂”—“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母亲难忘的时光

中间一排,左第一人作者的儿子王忠臣
1943年的某三天,从江西驶向西北的火车上,其中有一家人,衣襟嶙峋,她们一行六个人,其中的两个是大人,一男一女,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女的怀里抱着一个二三岁大的男宝宝,其余的是三个青年女子。
她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领着我的妈妈和三个叔叔抵达哈尔滨林甸县遭难的!
那种二三岁大的儿子就是当初我的女儿,她们是从广东来归顺我大伯父的一个儿子,因故乡连年旱灾,没办法生存,不得不逃荒到西南,栖身在同事屋内。
大伯父的儿子打看到有个叫黄窑屯的一个地主家用老兄,就介绍三个叔叔去他家里打长工。(四大伯给地主家放猪)一家人自此就搬进了黄窑屯住下了。(二奶奶当时还在青岛大姑家里)。
妻子隐约记得那种屯子是碱沟边,哪个地方的胡须(强盗)特别多,时常出没,有三天,有人高喊胡须来了,胡须来了!吓得人们不知所措,慌里惊慌的躲的躲,藏的藏,母亲也赶快叫儿子躺到炕上装病,用棉被盖上,不一会,胡须真的来了,她们四处抓小鸡,抓到小鸡就把鸡屁股使劲一拧,鸡屁股立时就两截了,抓够了,她们便扬长而去。
母亲说那时侯东碱沟(黄窑屯)经常有狼出没。狼夜晚下来能偷偷的把猪击退,你据说过吗?狼是这样把猪击退的:狼咬着猪的眼睛,用尾巴鞭打着猪,猪也不敢鸣叫,就这样乖乖的让狼给赶跑了。
那时侯黄鼬也好多搭彩钢房多少钱一平方,到了夜晚偶尔挪到人们的家里,不管挪到谁家,就钻到鸡窝里揪出鸡也不吃,把鸡压死,喝完鸡血就跑了。
黄鼬能够诱人,这事是真的,人们在灌丛子上打草时侯,就把黄鼬也给砍死了。据说黄鼬能释放一种哪些东西,就把那种砍死黄鼬的人给迷倒了,被折服的那种人就说:“我们在山上住,离大家很远,大家为何把我的孩子弄死。”人们自此都吓得再也不敢得罪黄鼬了。
五年后

林甸解放了,政府领导穷人闹农地革命,政府的党员组织群众一起开会议,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清算斗地主,界定成份。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四个阶层。如何界定呢?1)雇农,就是一无所有;2)贫农,就是租地户,没有农地,只有生产资料;3)中农,就是有农地,有生产资料,自己的地自己种,不帮工,不欺压人;4)富农、地主,就是占有大量的农地,拥有生产资料,雇长工、短工。
斗地主分田地:把地主的农地、房屋、生产资料、还有浮产(浮产就是毛毯、箱柜等)都分给了雇农、贫农。
母亲家里那年分了3间房子,10垧农地,还有毛毯,母亲说他当初盖上分得的毛毯用手一摸都是溜光溜滑的,用现今的话来讲那可能是对襟面的吧!分了田地,咋种呢?政府组织搞互助组,几户为一组,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有马的出马,有车的出车,相互换工。有个标语是:工换工,不放松,齐心协力把地种!那时侯的地就是这样种的。
农户有地种了,收获的粮食都归自己所有了,生产积极性也高了,生活也好了。
母亲家里人多,劳力多,地多,几个叔叔都肯出力干活,都是笔记本分分的庄稼人,没几年的时间,就置办了车和马,爷爷和三大伯、四大伯也分别成了家。
解放后推行了农地变革,老百姓都翻身了,分了农地,生活都衣食无忧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二奶奶王忠来就报考出席了人民解放军,当初他才19岁,从西北打到广西岛的战斗中,都有二奶奶的身影,后来他还出席了北韩战争,又在军队入了党。二奶奶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现今二奶奶已是90多岁高龄的奶奶,身体还很稳重,儿孙绕膝,过着幸福的晚年。我能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奶奶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1956年,国家推行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建,农业搞合作化,创立了中级合作社,由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以自然屯为一个经济单位。
各家各户把农地和生产资料都以股本的方式投入到合作社,集体生产,集体经营,按劳分配。
第二年,又创立了中级合作社,叫派出所,原先的中级合作社叫小队,小队的生产经营活动由分局统一管理。
1958年,组建人民公社,毛主席还给提了词叫“人民公社好。”
母亲8岁念书,中学是十年学制,他念了五年。
那时侯有文化的人甚少,母亲其实没上几年学,但他自己也阅读了不少书籍。

1955年10月份,母亲忽然接到村里的通知,让女儿到区里工作,由老同志率领着下乡。去的时侯都是自己背着行李,走着去,食宿都是在同乡家里,喝水是要付给同乡餐费的,每顿饭也就是1角钱。妈妈第一个月的薪水开了18块钱搭彩钢房多少钱一平方,当时的心情乐得都不晓得咋比喻了!
一晃到了十二月份,撤消区政府组建乡政府,原先区政府的人员由外县统一分配,母亲就被分配到了工行工作。
1957年4月,党开始搞反右运动,发动群众提意见,帮助党反右,当时叫大鸣大放,有意见可以公开的随意提。妈妈坦承不讳说:“统购统销,给农户留的口粮不够吃,合作化把农户都整到一起吃大锅饭,垄沟里找豆包都找不着了”。
运动后期,妈妈说的那些话遭到到了批判和斗争,她们批判父母说:“你说的那些话是右派反人民,左派言论。”围攻批判一段以后,就叫妻子写右派反人民的检测材料,母亲认为很委屈,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共产党还让自己出席了工作,如何会反共反人民呢?说的这些话只不过是提意见而已。
最后她们给儿子定性为反党分子不戴帽,给了两个月的薪水,叫儿子退休回去。
1978年,党对这种错划左派的人平反纠正,平反的推论是思想认识问题,母亲当时是有了工作,就没在恢复原工作。补发了母亲三个月的薪水并给与了提高三级薪水的待遇。
母亲还记得1958年在建行下放后,回到实验中队务农,当时的中队政委叫朱连生,他跟妻子说:“现在正搞水利建设,全中队的人都挖双阳河去了,你也去吧。”他就给女儿买了一双靰鞡(wula)鞋(这些鞋是鞋壳里絮上草穿的一种鞋),就把女儿打发去挖双阳河了。
挖河的人,孤零零的一片,有十几里地这么长,如同一条长龙,一眼望不到边。工地上沸腾了,喊着标语,人挖肩抗,打夯的标语络绎不绝,震耳欲聋:“同志们,加油干,赶快修完把家还”。还有一个标语:“苦干、实干加巧干”。还用哪些天上飞的(滑车),地上锥的(就是用车轴碾成尖,几个人抬着往地下锥地)等工具,土层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就被锥出来。正是十冬十月天,人们也不嫌冷,干的勇士朝天,满脸是汗。人们吃的饭都是小麦面的大锅盔,冬冷天的都把大锅盔冻的有冰碴了,午睡都是在冰凉的房间里,在地上铺上麦秆,都穿着大衣外套午睡,就是在这样坚苦的条件下,人们还是拼劲爆棚,没有人嫌苦,没有人嫌累。林甸人真是了不起,我为我是林甸人而倍感骄傲、感到自豪!
这个工程仍然到新年前夕胜利完成了!每位人的手臂都戴上了一朵大红花,排着长长的队伍,如同人民解放军打了胜仗一样,自豪的回到了家!
双阳河是通往牡丹江油田生产用水的水利工程,它惠及了两岸的人民,当地人用双阳河的水养殖的小麦除了给当地的百姓降低了收入,还让林甸人民吃上了非常可口的炒饭。
这一年,国家提出标语,鼓起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开始了,有的人就喊出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卫星(就是说大话),亩均一万斤。
生产队组建了饭堂,就不让在家里做菜了,都到生产队的饭堂喝水,这就是当初的所谓吃“大锅饭。”当时又掀起了大冶炼铁的风潮,建了小转炉,就连个家的锅都得拿去炼钢,由于家家户户把锅都拿去炼钢了,这就是当初所谓的“大冶炼铁。”
母亲挖双阳河回到家,分局长就找到女儿,让他去20颗榆树(三合乡胜利村)那儿的水洼去打苇子。那时侯都吃不饱饭,跟父母一起去的伙伴也不晓得从哪弄的哈士蟆(蛇肉)来煮着吃,咬一口白花花的油往内翻,母亲宁愿饿着腹部也吃不下,吃到嘴巴就想吐。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晓得打了多少苇子,就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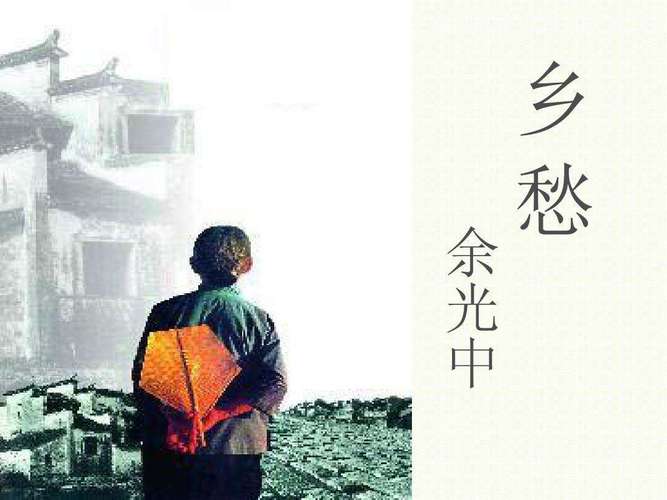
母亲回到了家,过了不长时间,中队长又找到了母亲,还是让他去打苇子,母亲不想再去了,也很吵架,“为啥总让我一次一次的去外边干活。”当时正赶上59年两年困难时期的开始,全省产生了一股盲流潮,(盲目流动人口),大批的流动人口涌到了大中城市去找工作,当时母亲年纪小,不够补选年纪,所以就没有选民证,(选民证在当时就相当于现今的身分证用,只是没有照片),母亲就借了一个名叫肖利修的选民证,就挪到了长春市去了,就用肖利修的名子在外边找活干。
长春有个盲流收容所,专门给外来的盲流安排工作,母亲就去了盲流收容所登记找工作,收容所就给安排到了,做打米工,当时粮食的包装都是用麻袋装的,每袋180斤,母亲年纪小,体格弱,根本就扛不动,心中很不是滋味,就有点不想干了,一起干活的伙伴们就跟爸爸说:你别跑了,我们大家帮你,扛不动你就给他人抬盒子,对付着干吧,当时母亲很感动,就留了出来。
母亲爱好打网球,下了班就天天泡在足球场,足球打的也不错,投球很准,就出席了厂子的足球队,常常和外边的球员出席赛事。当时厂子有个青年总支部长,对母亲印象很好,母亲就对校长说:“我年龄太小了,干着很费力,不想干了,想走,”书记说:“你别跑了,你原先在农行干过,有底子,我找领导商量商量,瞧瞧能不能调换一下工作。”没过几天,局长就通知父母去会计股工作了。
母亲在哪里干了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同学,他说他家在天津,他要回上海了,问爸爸有没有想去的意思,母亲当时想上海似乎能比这有更好的工作,也许能多挣些钱,就答应跟那种人去了,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赵养才的。她们一起坐上了驶向南京的列车。列车快到上海的时侯,发觉领她们去上海的那种人不见了,妈妈的衣物、包裹也都没了,这时妻子才发觉受骗了,爸爸就惊呆了。
母亲和赵养才在广州南站下了车,她们倆个人双眼摸黑,头上的钱也没了,还找啥工作了。赵养才在东站里捡了一把废旧的车票。他家是福建省高唐县的,往南走,母亲往北走。她们俩个人就在废旧的车票里找到了一张往南去的车票,一张往北京去的车票,母亲喃喃的说:“我们就用这两张车票回去吧。”
当时正是12月份,那时天气比现今冷的很。赵养才头上穿了双棉皮鞋,还穿了一件棉衬衫。妈妈脚上只穿了一双夹衬衫,裤子也被那种骗局取走了。父母就跟赵养才说,咱俩换换鞋吧,你往南去越走越暖和,我往北去,越走越冷。赵养才跟妈妈关系不错,就跟爸爸换了,还把衣服也给了父亲,就这样,她们两人就分别找驶向回去的列车了。
母亲就用那张捡来的废旧车票蒙混上了列车,到了北京,他身无分文,又冷又饿,母亲毫无办法了,就想把头上的衣物脱出来换口饭吃,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女子,母亲就跟他说:“我让人骗了,也没有钱买吃的,饿得都快受不了了,我想用衣物换你点钱和分币。”那人听妈妈说完,迟疑了一下,又看了母亲一眼,说:“行”。母亲就把鞋子从头上脱出来给了他,换了几块钱和一斤分币。妈妈用换来的钱和分币买了两个窝窝头,这是母亲受骗后吃的第一顿饭。
母亲在南京南站徘徊着,琢磨着如何能够回去,母亲想:只要是往北去的列车,不论是哪趟车,有机会就得上。母亲就到北站的进站口,趴在围栏上见到了驶向长春的火车正在进站,那时侯进站口的围栏不高,母亲趁人不注意迅速的跳过了围栏,随着上车的人流就上了车。幸而当时车厢里非常拥挤,没有查票。在列车上,有一个女同志领着一个小男孩拿着个小包裹坐在丈夫身后,母亲想:只有借这个女同志的光才会出站口。于是就跟这父子倆人问话,母亲问她到哪下车,她说:“到哈尔滨下车”,母亲就说:“咱俩是一道,我也是。”到了站,母亲帮她拎着包裹一起下了列车出了站口。
到了长春,母亲又回到原先的那种厂子,找到了一起干活的朋友,他叫阴增全,跟他说了前后的经过,阴增全就领着母亲去饭堂吃了顿饱饭,又给了弟弟十块钱让儿子购票回去。母亲就这样费力周折才回到了家。到如今,母亲还对哪个好心的朋友念念不忘。
十五年后
1958年后期,接着就是两年自然水灾,人们喝水基本上就吃不饱了,都得拿一半菜来弥补果腹。每人每晚四两粮,饿的腿都发軟,连活也干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大家就用玉米叶子、苞米瓤子、还有豆秆用锅子熬淀粉吃。
做法是这样的:把豆秆和玉米瓤子、苞米叶子置于锅子里,添一锅水,再放上食用碱,用着火煮,直至把这几样东西煮成粥一样,用布盒子过滤,把挤出来的臊子再度沉淀,把里面的清水倒掉后,剩下干的部份就叫所谓的淀粉了。大家就拿它来果腹,口感是又苦又涩,无法下咽。
母亲又挪到地里拣到了干青菜帮子,取回家用水如何都煮不烂,母亲就把它碾碎了吃,但还是嚼不烂,一咬都硌牙。也不晓得听谁说的榆树皮也能吃,母亲就去扒了一些来煮着吃,煮下来一看,天啊!一锅黏条,根本就无法吃。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农户也从不挪用粮食,都把地里打的粮食送交了国家粮仓。
生产队留作来年开春种粮的玉米种子,都是分到个家保管,两穗玉米叶子一系,都搭在屋内的房樑上,人们就是饿着腹部也没有一家、没有一个人动生产队的玉米种子的。那时的农户是多么的敦厚老实、多么的令人可敬啊!
就这样人们艰辛的度过了一个冬天,一个夏天。
母亲在生产队干了八年。哪个年代生产队干活都是跟随太阳走,每天天没亮,就有专门的打更到各家各户的门前高喊:“天亮了,上去干活了。”下午干活的时侯,就开始敲钟,钟就是用车轱辘上的模杯挂在半空树干上,到了上工的时间,就开始敲上去,人们看到声响都去干活了。等太阳落了山黑了天才收工。这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
哪个年代种粮全是用渔家肥,根本就没有农药,也不用化肥。生产队长期累月的积肥,一个大粪堆都够上几百亩地用的,过了中秋就开始用镐,一镐一镐的把粪堆刨开,把刨出来的粪用马车都送到地里,每隔十多米就卸一小堆,(种粮前再把粪扬开,这就叫施追肥),从远处看地上像长下来的千奇百怪的香菇一样!
那时侯的粮食和水果才可谓是无污染、纯红色的乳品!
哪个年代种粮都是人跟随四条腿跑,
种粮是用弯钩犁,弯钩犁的后面系个横杆,横杆两头系马套,一边两个马套,一个短的一个长的,一边套两个马,两侧就是套四个马。犁地时侯,赶套(赶马)的人一声令下,四匹马一起猛力向前拉。旁边还跟随扶着犁杖的、点种子的,紧跟随就是压磙子的。从冬至开始种粮,到小满基本上就种完了。有句俗语说:五月端午麦在前,五月端午麦在后,小寒到小满,种啥都不晚,过了夏至,不可强种。直至现今农户也是根据这个农时种粮的。
哪个年代也没有收割机,农忙割地时,都是人工割,弯着腰右手捉住庄稼,左手拿着镰刀,一刀一刀的把庄稼割出来。要是割花生,豆荚遇到手上,手就跟扎了刺一样疼。都不敢直接用手抓,都得戴上手套。一条垄割到头,不晓得累的得要直几回腰能够割完。人们把割出来的粮食都捆成捆码成垛,垛在地里,一垛一垛的都跟小山似的这么高。
哪个年代也没有打浆机,地里的庄稼都是拉到场院(打粮的场地),像高梁、谷子、玉米棒、小麦等,都平铺在场院上,之后用马拉着石头磙子,在场地上一圈一圈的碾压,直至把秆儿上的粮食压净为止。之后把没有粮食的庄稼秆儿挑下来扔到场外,再把压下的粮食攒(chuan)成一堆,看好风向,用木锨(xian)把压出来带糠的粮食一锨一锨的抛在空中,粮食有重量就落在了地上,瘪(bie)子和草末子都被风吹走了,地上的粮食用筛子筛过以后就装进了箱子里。
哪个年代粮食加工是没有机器的,都是用马拉着用石头做的磨,还有碾子。磨是加工面儿的,碾子是加工米的,三天只能加工二三十斤,各家各户都排着号等着加工。只有养牛的人家春节时能够杀一头猪,有的人家把肉烤制成鱼干,留着之后吃,有的人家,把肥肉都焅成了荤油,都焅两大坛子,留着长期吃。
哪个年代的路都是土路,桥面泥泞不平,一到下雪天,马车在土路上走过都压出了深深的车辙,路上都是烂泥,赶上有坑的地方,都会坞车,往外坐车的情境跟赵本山演的相声〈三皮鞭〉是一样的:车老总坐在上面手里摇着皮鞭一甩,嘎的一声,高亢响亮,嘴巴还喊着:“驾喔,驾。”马儿就拚命的向前拉,旁边还得跟随几个人用力推。就这样就能把坞的车推出去。
人在泥路上走,都把鞋给粘掉了,下大下雨得穿上长靴。雨停了,小孩们穿着五颜三色的雨衣挪到水里趟水玩,雨衣在水里如同各类颜色的小金鱼儿游来游去。有时侯赶上下洪水,桥面上都是积水,壕沟和桥面的水都连成了一片,得拿着个木棍拄着探着路走。
哪个年代林甸通往泰康这段路的交通工具是没有车辆的,只有马车,母亲记得有一次去泰康父亲家回去,就是坐的马车,车上还坐了一车人,一百多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大半个夜晚,从早上六点多仍然走到十二点多,即使是夏季的季节,还是冷的都偎依在一起。

不晓得那个领导想的办法,林甸通往泰康的路铺上了木轨,就跟铺铁轨道是一样的,下面铺上轨枕,轨枕上面再铺上木头的轨道。走这些道儿的车叫“轱辘马子。”这种车跟矿井巷道里运煤的车相像,结果修成了,也即使报废了。
哪个年代住的房屋都是土平方,每年入秋前要用黄土泥拌上(yangjiu就是干草)把房屋的整个墙面抹一遍,是为了御寒,就是这样,阳台上的玻璃还是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到了夏天,必须得到有碱土的地方拉碱土抹房盖,以防夏季下暴雨把房盖冲漏。
那种年代也没有电,家家都点个煤油灯,从远处往外边看,家家屋内如同飞了个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的!
那种年代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坚苦的条件下生活着,勤奋、朴实、善良的那代人承载着历史的使命与苍凉,为创造美好的未来不停的拼搏着!她们创造的价值,仍然能在永恒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最闪亮的一刻!
二十二年后
到了1965年,信用社缺人,就把女儿找去下班,干了几个月,把儿子调到外县人民建行会计股,仍然到1976年又调到外贸做财会工作,直至1992年退职。
母亲对现今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深有感慨!
时光似箭,几六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发展了,强悍了,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农户种粮都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解除了艰巨的体力劳动。饭桌上也是吃啥有啥,没有你吃不到了,只有你想不到的。彩钢房、保暖房代替了土坯房、茅草屋,过去当笑话讲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都成了现实。由过去的土路都弄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道路四通八达,出门有铁路,做客机,各类交通工具应有尽有。林甸这座小城,已高贵的换上了新的华装!
母亲一生曲折,经历了时代的演进,见证了社会的发展,享受着新生活。即使如今是衣食无忧了,但父亲还常常嘱咐我们,不要浪费粮食。
看着生活在良田与白云间的农户,听到她们辛劳耕耘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水果,听到她们任劳任怨农活的身影,不能不让人感叹和崇敬,勤奋而伟大的农户,有了她们的劳动果实我们才赖以生存,在爱护粮食的同时,更应当赞扬农户,她们是中国的脊梁,人民的骄傲!要珍视明天的幸福生活。要有知足的心!
母亲已年近八十,仍然是精神矍铄,每晚生活的特别快乐,也觉得很幸福,他对现今的生活很满足!很感恩!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9年出生,1986-1988年在外贸商店就职,1988-1990在林甸酒店下班,1990年回外贸土畜站,2004年退职在家。
—征文链接—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二手彩钢网看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