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老家||耿志梅:黄土高原的前世今生
- 手机:
- 微信:
- QQ:
- 发布人:佚名
- 所属城市:重庆
信息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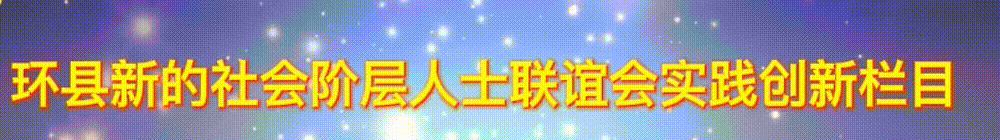

山里老家
作者|耿志梅·朗诵|苏海燕·编辑|牛玥珂
我家搬去黄土高坡,狂风从坡上刮过
——信天游
谚语:一代人不住另一代人的地方。
我们这儿把住宅叫“地方”,修筑住宅叫收拾地方。
自周人不窋率族人走出地穴“陶复陶穴以为居”,人们在有食充饥、有衣蔽体的前提下就开始和地方较上了劲,一代又一代——
山梁塬峁,千沟万壑。黄土高原奇特的地形地貌决定了人们居住的特征:因地制宜,就坡顺崖。
我家旁边有一座高山,是我们迈向外边的必经之地。每每站在这个山峁顶上,整个村庄尽收眼底——一弯如同游蛇的沟渠奋勇将山划开,新旧村落洒落在河堤两边的半山腰上,抢鲜入眼的倒是这些已经废弃的四合院,一只只的,张着黑黝黝的大嘴巴,透过浓荫杂树凝视着,将这方天地的前世此生都盛放到她深沉的眼神里。
这种穿透历史的双眼,就有我家的老庄。
若要往上溯源,我家多年来住的地方开始于我的太奶奶。
太奶奶须要自立门户了,扛着一把镢头他在山梁沟洼里兜兜转转,眼神落在了半土坡这个三面皆是沟壕的地方,一镢头挖下去,一个家族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
太奶奶及父亲是怎么蚂蚁筑巢般的凿土成窑,我只能想象,单凭那几近二十米高的崖(nai)面,阔展的庭院,十来米深的几孔大窑,在当初纯人力农活的情况下就已足见其工程的浩大与辛酸了,其实是举全家之力倾其多半生才得以完成。
四合院是朴实的,黄泥一抹,即使家装,火炕土锅头,是最基本的设施,窑掌里由高到低留两个土台,盆盆罐罐就有了安身之处,人间的烟火气便在这儿弥散。
四世同堂,箪石瓢饮,鸡埘鸭寮,自是须要三五三居的。我家大小四孔窑,三处住人,一处拴畜牲兼磨房。大婶离婚时娶亲的女客没处接待,就提早在这个磨窑里打了一个炕,打扫干净,临时当成贵宾房了。事后据反馈回去的信息称,顾客极其不满:进门是炕,磨台竖立中央,窑掌是驴槽,一股畜牲的猪粪味自毋须不说,单就是晚上刚睡醒,挣开座骑回去的驴一头撞开门把他们差点吓成咯血疯。
风从崖头刮过,雨水磨蚀出了条条沟壑,青苔昏黄,茅草丛生,于是就要整修了。
一镢头一镢头的剪掉崖面上陈旧的土皮,再勾划出水波形的花纹,肩挑手抬的一筐筐往外运土,能借来一辆架子车那就是相当先进的工具了。窑上面铲掉熏黑的泥坯,再抹上一层和着干草的黄泥。一切都是极简的,就地取材,搭上的只是一把力气和泪水,物质短缺时代,只要有一把木柴,日子便有了气温与滋味。
不仅每隔几年的“刮痧锐化”式的收拾一次,以使因风雨侵蚀而残破的庄院重新变得“气堂堂”而外,母亲还有过大的“工程”:将所有的窑肩子全部摧毁重新砌起,由原先的圆拱形改成流行的圆形,上檐加几行砖做了花纹造型,还铺了溜水瓦。窑门也换成旧式的装板门,但是刷上了漆。
不知从那里买来一蒙自的旧式平柜和一张三斗桌,这是我家真正的灯具摆饰。后来又请来了石匠,要打两个大立柜,却受到了父亲的竭力反对,理由是:不能盛米不能倒面的,立在哪里高晃晃的像个棺木一样。执拗的老头疾言厉色不能制止锯末锯末的飞扬,干脆就整天拉着脸不理工匠以示谴责。
每每农活三天归来,洗去脸上的黄土,母亲就会蹲在门硷畔,装一锅老旱烟,嘎吱嘎吱的抽着,烟锅头里的烟柱缕缕上升,水塔里的烟也缕缕上升,小时候的我,往往认为这烟柱擎起了整个天空。
丈夫,妻子的弟弟的儿子,能有几孔冬暖夏凉的土四合院,窑里放几个盛着粮食的囤子,日子便觉富足而安心。
高天厚土,那细软而又坚实的黄壤土像温良憨厚的长者一样,用她宽厚的肩膀接纳宽容着她的儿子,任其纵横浑成,刮不薄、挖不透。祖传的四合院几易其主,修修复补,仍然冬暖夏凉,保障我们寒暑不惧,但老哥还是决定要建房了。
“出门靠走,不是上山就是翻沟”,恶劣的交通条件的阻隔了多少人关于建房的梦想,但老哥决然毅然。
打算工作从一五年前就开始了,庭院的几棵白杏树(是太奶奶还是父亲栽的?我没有考证)采伐倒,做大梁,做木门。还有打基子,农闲或则小雪天难以下地时,老兄都在打基子,一把铁锹一把杵子,将一方土台的土锤打成一个个土坯,摞起了多半人高的几溜长墙,以备砌筑之用,可以省却许多板砖。
椽与屋架都是在四五十里外买的,八月的沟渠,冰将化未化,春水回荡,正是难走的时侯。大婶以换工的方法请了七八个人拉着几辆架子车,鸡叫时出发,回去已是深夜,裤子已湿到脚踝处。
好在拉砖瓦的师父艺高手胆大,将车开到了门前的沟里边,剩下的一段坡道,只能人背驴驮,《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背石头,也就是这个样子。
依赖农地,却又时时都想征服农地的人啊,战天斗地满腔高亢,面对自然及不可控的命运又心存崇敬,即便谢土前都要祭土神、祭灶神、祭告天地,但求平安无恙。总算破土复工了,请来了一个技术工,自家人当小工,挖土打地基,担水和泥,抱砖送瓦,背部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双手磨烂又长好。三间土木结构房总算立上去了,青瓦红墙绿门,无瑕的玻璃窗,流行的金箔带绷顶,红色的涂料刷了炕腰。有别于黄土的色调和不同于四合院的外观结构,使其显的卓尔不群,从旁边山峁走出来一眼就将“上岗家”与别的人家分辨下来。
这三间房对我家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时一条沟几十里住的前后庄里只有两家有房,分别是历任的村长和前任的乡长,她们是公认的“能成人”。
可惜大婶没有住过他盖的房屋,自始至终他都搬去那种阳光极少能照到的小窑里。
大婶有两个女儿。
最先是大女儿废弃住了几代的老地方,另开宅子。
选址,顶管。
在现代机械的钢牙铁齿下,沉积了亿万年的黄壤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十来个小时即整出了一处场院。前几天二儿子说,请前辈看过了,这个地势呈龙形,后有靠山,前有屏障,九山环抱,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地,也算是无心插柳之作。
一切齐备,很快在南面盖起两间半倒厦、北面三间彩钢房——农村近几年流行这个,经济、便捷,也暖和。中间位置留着,等手头充裕了再盖。
过了一年,又拉来了砖瓦椽梁,五间正房立上去了,石膏板橱柜,地砖墙面,新型合金窗户闪着轻柔的金光,高墙大院,绕边再植几许松柏,四合院完整了。
二儿子参与家事后,三天,他站在庭院里一注视:这个彩钢房也太不上档次了,于是——拆。
自此,这个庭院就开始了拆与建的时代。
先是拆了彩钢房改成砖平房,顺便安装炉窑,撤除所有火炉。
南面做卧室的那几间倒厦不配整个四合院的知性了,一通操作,三座房屋知性统一了,一个完整的别墅。
房门外还有一方土院,雨天崎岖,做了护岸,铺上漏水砖,白蓝相间的围栏竖上去,用母亲的话说:做了个城儿沟的小广场。
围栏式的院门小且俗,换,新的房门宏大气派,肃穆的红色,梅兰竹菊的花纹,透出了几分优雅。
换院内外的行道树,炉窑换成电暖再换成空调。
每换一次,丈夫都竭力制止,最终无济于事,之后都惋惜无比:好好的都能用,晓折腾咋呢?
前天,妻子电话里说,家里又要收拾地方了。叹道:平常家里就在两个人,盖如此多干啥呢。
是的,两个儿子在市区都住房屋,老家平日就父母和姐姐在。
黄农地滋润的子孙,个别情结仍然承载在基因里、流淌在血脉里,不管被湮灭多深,总有这么三天,会火山爆发般的倾泻而出,势不可挡,例如四合院情怀。据说此次收拾地方是由于儿子想住窑了。
古老的农地又一次在机器的嘶鸣声中发抖上去了。
丈夫说:所有的棚圈都拆了,西边的房也拆了。
丈夫说:四个小车运料,拉了几天了农村彩钢房造型图片,还没拉够农村彩钢房造型图片,这把钱花的多的很了。
丈夫说:窑拉回去了,套上去就好了,省事的很。
丈夫说:光木柱和台阶的花岗岩就花了十几万,又拉回了一车玻璃,玷污钱呢。
丈夫说:灶房又要拆了,被正房新加的过道遮挡了一点,不好看。
丈夫说:……
工程还在继续,母亲关于“新新的就拆了扔了”的心痛和“钱花的多了”的担忧与日俱增。
我的老奶奶,一面气愤疾首的抗议他的“嘎杂子”孙子胡花钱,一面逢人就想说道说道她们的新地方。
姐姐也责怪:地方收拾的够够的了(够够:厌恶、厌烦之意),院大的冬天一下雨扫的把人能吓死。
窗前大雨飞舞,听着姐姐的牢骚,想着她们那又扩大了一倍的庭院,再瞧瞧自己的斗室蜗居,幸好自己没有寸土片瓦落雪,笑犹未尽,突然顿悟,哦嗬——,我的老婆呀,三天学堂未进,这凡尔赛上去也毫不逊色啊。
作者简介
耿志梅,兴县思源实验中学班主任,课余之余喜欢阅读,在书本中找寻人生的静谧恬淡。


主播风采
苏海燕,音乐教育工作者。一个一直深信只要想赢就一定能赢的知性随性而活的灵魂。从不借助从不找寻,只因此生平而不庸!
榕江夜听诵读者联盟招募中
每位人都有自己沉甸甸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会让我们心有戚戚焉,给与我们启发,也让我们在无形中获得力量。诵读和阅读虽然都是一种力量,可以是为了感恩生命中美好的遇到,也可以是为了诉说爱;可以是为了抒发心里的憧憬,也可以是为了弘扬新的希望。榕江夜听诵读者联盟招募中,欢迎您的加入,让我们共同牵手构建榕江原创文学诵读平台!
联系人:刘棹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二手彩钢网看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