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钢房多少钱 牛利利如火如荼:80后包村干部齐岩的乡村挑战与机遇
- 手机:
- 微信:
- QQ:
- 发布人:佚名
- 所属城市:重庆
信息描述
上海文学|牛利利《如火如荼》
原创牛利利上海文学2025年01月15日08:03上海

牛利利,1989年生,河北定兴人,结业于成都学院,哲学硕士;现居成都;中国画家商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长江文艺》《青年文学》《作品》《清明》《飞天》《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中长篇小说多篇,部份作品被选载;小说集《兰若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诗人出版社)。


导读
80后包村党员齐岩犯了难:去蜂农老姚家入户,问题没解决,又添了新麻烦;省领导下乡检测工作,偏又遇到林业工人生火烤火,落他一人在山坳待到深夜,还做了检讨……县里调整党员,他想捉住这个机会离开村庄,最终却也落了空。乡镇工作是如老校长写的那幅绘画“如火如荼”,还是“一团乱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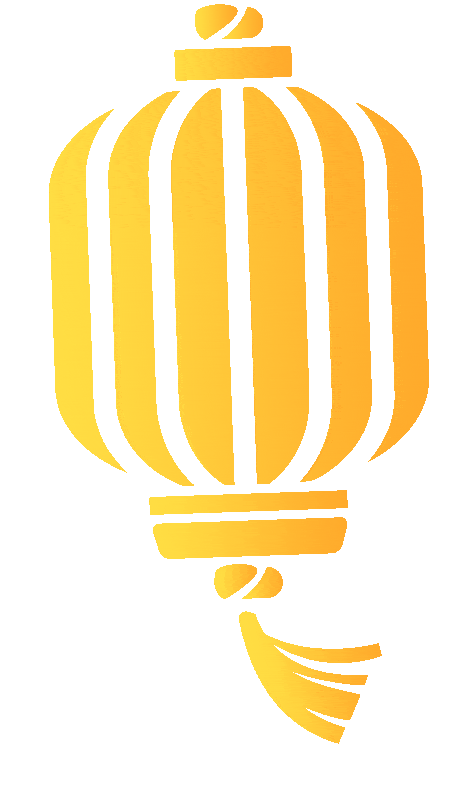
好看小说(短篇小说)(摘录)

如火如荼
牛利利
一
到处是胡蜂,吵得世界都漂了上去。老姚站栎树下,高举竹竿。竿头悬纱笼,无数蜂往里钻,远望如正在破碎的蓝色旗帜。远处有一顶旧帐蓬。河堤平整的地方都摆上了蜂箱。老姚收完蜂,走到车跟前,摘下边罩:“领导,有空来村上耍?”说着,手伸入后窗,夹烟的手晃晃。齐岩迟疑下,接过烟,说:“去你家入户,摸摸情况。”老姚“嘿嘿”笑了,说:“摸哪些?月月摸,天天摸,农户的尻蛋子都摸破了。”他也笑,下了车。
热风扑面,带着黄蒿的气味。齐岩帮老姚拉开防蜂服的拉链,说:“你才五十出头,头全白了。”“活着不容易。”老姚弹飞烟蒂,说。“你是太贪心。”齐岩拿话点他。老姚擦擦汗,冷冷说:“一大伙子全靠我一人。明强林校结业,嫌打工苦,三天到晚胡逛。大儿和你同岁,几年不着家。明霞嫁到外省,今年结婚,抱着两个娃回去了。妈妈都八十了,要我养活。嘿,我不老,谁老?”齐岩备好了话,到嘴里,又讲不出。老姚走到街边,提起碳钢摇蜜机,扛肩上。他让老姚把摇蜜机放他车上。老姚摆摆手,径直上了坡。他跟在后面,看见湖水声逐渐远逝。
一辆桑塔纳停下。后窗摇出来,冯春来探出耳朵:“小齐又入户?你工作举办得扎实呀。没驾车?”“停河堤了,走两步。”他笑着说,又问冯春来去干哪些。“给居民复检嘛。”冯春来又对老姚喊话,“老姚,你妈高血糖的药不能随意停,高压快两百了!”老姚“嗯”了声,步伐不停。
齐岩和老姚上了桥,走过方神庙。庙旁边龙旗猎猎翻飞。靠墙停着辆架子车,地上扔着空饮料瓶。车上躺下老光棍水雄。“老水叔,闲着呢。”他打招呼。“闲不闲,关你屁话!”水雄翻躺下,逼视二人。“有人惹你了?”他挡住火,问。水雄手撅嘴,油光的耳朵一扬,说:“就是惹我了。豇豆前年一斤一块四,今年跌成一块二。豇豆价钱降了,大家党员的薪水为何不降?”老姚单手提着摇蜜机,一手拉住齐岩,走开了。水雄跟在后头,高声浪骂:“偷我东西的,迟早吐血水死,别怪明日没提醒!”
到了姚家,齐岩擦着脖子的汗,气咻咻地说:“水雄嘴上不积德。”“他没后,积德没处用。”老姚说着,把摇蜜机放台阶上,把防蜂服叠整齐,又跑进卧室,取出搪瓷面盆。齐岩洗了把脸,用衣袖胡乱擦了擦。老姚妈妈拄着双拐,走出西大门,弯着腰,当心翼翼地下了台阶,问:“不摇蜜了?”“明天摇。”老姚把盆里的水浇在靠房檐的桃树下。老太太又说:“厨房有馍,你去吃。”老姚挥挥手,说:“别管我,你回房睡去。”老太太愣了愣,自言自语:“哎,老了,听不清,不知你说的啥。”西房传出电视声、小孩争吵声和苍老的咳喘声。
屋子乱极了。里墙摆着张木桌,红漆昏黄,上面堆着瓶瓶罐罐。红色大塑胶桶共六个,排两列,里头是牛奶。几只蜂正绕着桶飞。靠墙高摞着十几袋一百斤装的大袋蜂蜜。火盆灭着,墙熏得黑漆漆。老姚取了小桌子,纵火塘前,又倒了茶,递给齐岩。老姚端着搪瓷缸,先喝了一气。齐岩拧头看向四合院。庭院扫得干净,水泥地面反着光彩钢房多少钱,像一汪水。老姚说:“我惹了水雄。”“那他跟我斗嘴?”齐岩接着说,“自打我当了这个村的包村党员,够照料他了吧?今年我从县上给他要了卫生公厕的指标,他是一毛钱没花。前年,他种了猪苓,卖不出去,跑来向我倒苦水。我挪到文峰的草药市场,帮他联系了收草药的老总。”“你还年青。”老姚讽刺地说。
门外传来“笃笃”声,老姚妈妈拄着拐走入大门。她动作平缓,在疏密交界处,如泥塑通常。蜷曲的、满是疤痕的手伸到齐岩眼睛前。“小伙子,拿上。这是好烟。我晓得你是领导。”她迎合地说。他忙推却。“说哪些?我耳背,听不清。”她说着,转出大门。
老姚取出一瓶酒。齐岩忙摆手。老姚拆开酒盒,作势要打开。他说:“我要驾车的。”“找人送你回来。”“今天下班,我一身酒气回来,领导如何看?”他有贬低的意思。老姚放下酒坛。他此行的目的是拾掇老姚,可不知怎么起头。近来居民对老姚反映不少:有说老姚砍了旁人的杜仲树的,父亲霸道横行的,还有说他偷挖河沙的。前天,乡上黄书记领着人大的领导去视察牛肝菌菌种植合作社。一行领导刚出暖棚,一个居民正骑摩托路过,见有领导在,便告了老姚一状。事后,黄书记喊他去办公室,黑着脸,说:小齐,你是包村党员,要多下村走访入户,了解老百姓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现在居民跑我跟前申冤,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渎职?这几天你去跟姓姚的好好说说,硬拼;你一定让他收敛,别挂念着当恶霸,不然没好果子吃。他说,好的,校长。他不想和老姚硬拼,希望最好能像前辈过招那样,点到为止。
老姚的外侄女从西房跑出。小男孩三四岁的样子,扎着马尾,站在庭院里,望着齐岩,笑了。齐岩向小男孩招手。姚明霞抱着小孩子下来,喊:“梅梅,别走,外面有狗。”女儿回头看了母亲一眼,咯咯笑着,跑出了房门。姚明霞向齐岩打了招呼,出门寻孙女去了。老姚坐火盆前,慢悠悠地说:“有大人物去乡上。”“你如何啥都晓得。”齐岩有点意外。老姚说:“今早我去给我妈买药,路过乡政府,见黄书记带头扫路。嘿,堂堂主任,衣上全是土。现在,乡上领导是不值钱了。话说回去,你如何不去迎接?”“我躲都来不及,嫌烦。”“活着就是个烦。”老姚给齐岩添茶。姚明强走了进来。姚明强瘦长个儿,穿着布满闪光片的T恤,脚踏布鞋,见了齐岩,也不打招呼。姚明强提起地上的酒壶。“干啥去?”老姚喝问。“找黄蜂去耍。”姚明强攥着酒壶手腕,跑出房门。
“那个公牛也是怪人,”齐岩决定从姚明强入手,切入主题,“一院旧宅不住,躲林子里,鬼一样。他在林子里的住处我去过。一间彩钢房,不通电,靠太阳能板给手机、台灯充电。明强年纪小,贪玩,辨不了是非。你让他少和黄蜂混。”老姚仍笑,目光却冷硬,皱着眉,半天才说:“他爱跟谁混就跟谁混,当老娘的也管不了。”
三人都沉默着。天突然阴了,起了风。老姚抽出根烟,大手指和手指捻了捻,又放眼睛下闻,说:“我清楚你为何来。有条死狗去找黄书记,你就来了。”“有人说你砍了旁人的杜仲树,还说……”“放他娘的屁!”老姚火了,从灰烬中抽出火牙签,敲着地面,高声说,“他说是他的杜仲,大家就信?人人都有一张口,偏他有理?去年杜仲价高,一斤四块。有钱你们一起赚,各凭能耐。我勤奋,卖得多,有人眼馋。笑人无、恨人有的东西!就连老光棍水雄都眼馋,说我卖的是他家的杜仲,看我耳朵不是眼睛眼不是眼。黄书记不了解。小齐,你当包村党员多少年,也信那些?”
二人对视着。老姚拄大火牙签,眼露凶光。不过一个回合,齐岩便觉落了下风。他腹中有火蹿起,下巴上的血管跳跃着。他想,硬拼又怎样?得让老姚收敛,这是主要目的。“你先不急着吵架。一件件一桩桩,我们还得接着说。”他说。“来来来,一件件说,看够给我判几年?去他妈的!总之我压力大,不如入狱,至少还管三顿饭。”老姚扔下火牙签,两臂伸开,像一只白色的大鸟。他“哈”了一声,扭过头,看向庭院。老姚妈妈站在檐下,弓着腰,望向下房。西房里静悄悄的,电视声、小孩争吵声都不见了。房檐跑过一只花鼠。花鼠爬上墙头,坐在一株摇动的瓦楞草下。
他正要同老姚死磕,电话响了。他长呼出一口气,躺下出门。庭院里,老姚妈妈说:“厨房里有馍,你是顾客,吃上一口。”他小声说:“姨,我吃过晚饭了。”
出了院门,齐岩回过去电话。电话里霍燕燕告诉他,她妈明日到市区,她妈来一趟不容易,他最好能作陪。他口上应承,说,正在忙,完了细说。他心情不好,怕霍燕燕听下来,误以为不愿意接待她妈。事实上,他的确不喜欢她爸爸。
齐岩走入农户广场旁的亭子里。白色的鸟落在枯萎的树上,感伤地叫着。凉风吹拂,他倍感沮丧。水雄拉着空架子车正路过。水雄酒醒了,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快步走过。很快,白雨落下,浓荫横绝四周。
雨中出现一个人影,是皮老师。皮老师五十多了,当过几年村小的公办班主任,后来仍然务农。皮老师走入亭子,拍拍裤子上的泥点子,说:“你真是好兴致,一人在这看雨。”“皮老师忙啥去了?”他问。皮老师取过背篓,让他瞧:“上山挖药去了。收获不大,挖了几根沙参、两块当归。”皮老师的脚伸到台阶上,蹭掉鞋头的泥,点上烟,扭头看雨云,感慨:“不知道西安下雪没?”他晓得皮老师又要讲他兄弟。“上个月,兄弟给我买了剃须刀,快件到的城区。西门子的剃须刀,有三个头,两千多块钱呢。我是老农户,用这么贵的东西干哪些哟!”皮老师笑上去。他回想起刚当包村党员,第一次下村,在皮老师家喝水。皮老师吸溜着面粉,讲自己兄弟多么优秀:获过国家奖励,被主管科教文卫的副书记会见,论文发表到了美国去……听了几年,他眼睛生了茧,一度见了皮老师就绕着走。明天,他不认为烦。他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兄弟,为兄弟骄傲,这是应该被尊重的。“皮老师,上次我去西安提早跟你说,带你去见兄弟。”“兄弟满世界跑,有一年春节他还在英国讲学。碰面不容易。”皮老师吹熄烟蒂,抽泣,又讲起他为了兄弟上学院,到此地当上门岳父的往事来。
齐岩再度走入老姚家。“呀,小齐,你跑哪里去了?我正要去寻你。”老姚站在檐下,作出副震惊的表情。“路上走了走。”他说着,走入上房。火盆里生了火,碗口粗的木头烧得正旺。他向火而坐,不一会儿就倍感外套上飘起水汽。老姚走入来,将棍子架在火上烤一会儿,又到旁边,对着天光,摩挲上去。“昨天砍了根木头,计划做擀面杖。你看下,这木棍如何?”说着,转身把竹签递给他。“压手,宽度也适宜。”他说。老姚重新倒茶,坐下,说:“等擀面杖做下来,献给你。”“我吃饭堂,又不煮饭。”“等你成亲了用。去年该结了吧,嗯?”老姚亲密地拍拍他的膝盖。他想,老姚是个硬茬子,之前像是要杀人纵火,可这会儿又和风烟雨。
“有句话怎样说来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的人不好打交道。”老姚扯起邻里长短,言外之意是他也有委屈,不过为人老实,不告刁状。房内越来越暗,塘中的火焰腾跃。人与物的影子都在晃,如风飞过疯长的荒冢。齐岩一阵恍惚。凉风卷进明亮的雨帘。
齐岩不说话,拿出手机。工作群里发了视频:黄书记穿着雨鞋,站条幅前,指挥党员们清除渠里的垃圾,起初尖细的叫声在风雨中更显稚嫩;乡农机具中心的赵文斌校长提着两大袋垃圾,直奔垃圾车;副局长章月涛叼着烟,拿着柴刀,偷瞄校长,不铲粪便,一个劲儿铲着粪便旁的积水。见到这里,齐岩忍不住笑了。老姚又换了话题:“听人说,近来乡上要提拔党员。”“不说这。”他摆摆手。老姚又说:“现在干哪些都靠关系……”
齐岩几次想把话题拉回,又被老姚扯远。老姚取出袋花生,埋进灰里,煨上几分钟,用火牙签夹出,一一挖开、剥好。老姚将花生仁放到碗中,又浇上蜜。老姚递过来牙签,说:“好东西,活血补肾。”他吃了两口,说:“自我包村以来,同你打交道最多。居民都说我俩关系好,你别让我责怪。”“人抬人高,土抬墙高。这道理我懂。”老姚说。
齐岩看了看时间,躺下,说:“今天迟了,我要回家加班,完了和你细说。”“留下喝水吧。”“不了,回饭堂吃。”他站在旁边说。“我挖了株小罗汉松,得空给你送去。”老姚贴过来说。“那是国家保护动物!”他身子两侧,避开老姚,吵架地说,“最近警车来回跑,你以为森林公安吃闲饭的?”老姚讪讪地笑了,说:“领导明天很严肃。哦,我还有事要麻烦。”“别叫领导,就说啥事?”“你晓得我一你们子人,老的、小的都靠我。我手头紧张。去年中蜂种植补助涨了,有一万块钱。你把我报上。”老姚说。他想了想,说:“文件要求,规模要在百箱以上。”“啥都按文件来,月球还转不转了?这还不是动动笔尖的事。”老姚说着,给他撑开伞,又说,“我晓得你心情不好,这会儿推托不算数。”
齐岩走到海边,袖口全湿了。他坐在车上,打开空调和雨刮器。他愕然看着前方。雨中峭壁苍然,蒿草碧绿。他想:明天去老姚家入户,问题没解决,又添了新麻烦;以老姚的为人,拿不上补助肯定斗殴。他认为头痛,追忆起刚到乡上,老校长找他入职谈话的场景:
老校长办公室的墙壁挂着一幅行书。他看了一会儿,认为最后一字像“茶”。小齐懂绘画?老校长笑吟吟地问。他急忙摇头,又低下头,包里拿出电脑。老校长讲上去:乡镇工作压力大,你别想像得太美好;往上全是管我们的领导,因而说,里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点点头。老校长继续讲:我们举办工作又要直面群众,群众很单纯,群众工作很复杂……谈话结束,老校长躺下,望向那幅绘画,笑了笑,说:字是我写的,涂鸦而已,不成章法;有时我想,把“如火如荼”换成“一团乱麻”,其实更贴切。
手机又响了,是校长黄杨。“你人在哪里?我们都快忙死了,三天不见你人!”黄杨气呼呼地。“书记,我在村上,刚去入户了。”齐岩赶快解释。黄书记“嗯”了声彩钢房多少钱,心态好转:“小齐,你如今哪里都别去,就待村上。省上的领导换路线了,去大家村。我这阵在路上,再有半小时到村上。”他一句“好的”还没出口,黄杨就挂了电话。
齐岩掉转车头,又进了村。村口立着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写着:“银水湾村欢迎您!”

海男书法作品
(摘录)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二手彩钢网看到的,谢谢!!